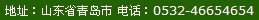|
毫无疑问,“诗与远方”是作家的重要标签以及孜孜追寻之目标,“在旅行中阅读世界”则被誉为写作者和其拥趸的最佳享受,前者身在其景而作而歌,后者读之宛如身临其境,他们精神相遇后共享的,正是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时空风貌、人生经验、生活样态以及内心隐秘,因而在那“理想的远方”共赏欢愉。 鱼之于水,水之于鱼 风物与作家们的“鱼水”之欢 《牛津英语辞典》里对旅行写作的定义是,“有特定形式、风格或目的的,特色一致的文体类别”,这略带僵硬的英式解读自然不能完全概述游走在家乡与世界之间的写作者与笔下地理空间的种种情感,无论是出身之地还是到访之地,写作者与地理风物之间的关系犹如“鱼、水”,不细致品读不足以知其况味。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作品也是地域文化的产物。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人文风情总会浸润并影响着作家的写作思路与风格,绝大部分作品里都张扬着浓郁的在地文化。甚至于,很多作家生平的地理空间跨度决定了其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叙述,那并不止于一种故事发生与存在的先决条件,亦是作家本人的价值取向。比如屈原笔下就满溢着楚国风物之美,《离骚》有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正是楚地之人与花草树木之间的特殊关系,屈原以之喻自己崇尚的高洁。 作家对心仪之地的情感温柔而坚韧,哪怕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将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美好景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可以让他的故事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地,自己的心绪却不愿真正走出“南美的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十分深沉,我失望或痛苦时,一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是产生虚幻的感觉,便是听到庭院深处传来的吉他声,或者同生活有了接触,这时我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 写遍藏区故事的阿来曾在《遥远的温泉》中这样写道,“这是年4月13日,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在东京新大谷酒店的房间里,看着初升的太阳慢慢镀亮这座异国的城市,看着窗下庭院里正开向衰败的樱花。此时此刻,本该写一些描写异国景物与人事的文字,但越是在异国,我越是要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于是,早上6点,我便起床打开电脑。一切就好像是昨天下午刚刚发生一样。”至今,每年的6至9月间,阿来都会在青藏高原一边游历一边写作,这片土地是他永亘的创作源泉,“我更多的经历和故事,就深藏在这个过渡带上,那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干脆在作品《押沙龙,押沙龙!》中为自己虚构的以家乡河流命名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绘制了一幅地图,“它的面积为平方英里,人口中白人为,黑人为。这个县唯一的业主与所有者是威廉·福克纳。”这简直是作家与地理时空的最高境界,“哪里都找不到他,但他又无处不在。” 那时风物,那时人间 那些笔下蜿蜒的“理想”之地 作家们往往不会困守一地,他们怀揣各种情愫踏上旅途,足迹越来越深远。甚至于,普遍存在的各个领域的“南北”之争、“城乡”混合也因此在文学界显露。一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斯达尔夫人所说,“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又如苏童所言,“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的那一侧。” 按照文学评论家艾伦·塔特的说法,“一个作家,若想概括整个大陆,包罗万象,他将会一无所有;一个作家,若执着于某片土地,有所选择,有所舍弃,他反而获得了一切。”其实,无论成名与否,作家们大抵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仅以中国作家而言,就有沈从文的“湘西”,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黄土高坡”,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等,这些亦实亦虚之地是他们故事的重要策源地。 当然,也有的作家甘于叹赏旅居之地的一份安逸,如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像什刹海,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薰蒸。” 因了写作的缘故,作家对所处之地的观察与体会是细腻而深刻的,他们对笔下之地的情怀既可是纯粹的喜爱,也可是复杂的审视。日本小说家村松梢风笔下的上海即是一例,在纪实性作品《魔都》里,村松梢风描绘了自己所观察到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全景,将之描述成一个具有魔力的城市,大亨与小民共存,五光十色与暗黑隐秘并行,让人向往又恐惧,“魔都”之称由此而来。观景亦可观人,在本土作家木心笔下,“魔都”的魔力是这样一番光景,“上海是人的海。条条马路万头攒动,千百只收音机同时开响。杨四郎动脑筋去探母,打渔的萧大侠决定要杀家了,黄慧如小姐爱上车夫陆根荣,杨乃武、小白菜正在密室相会。长达十小时的沸腾夜市,人人都在张嘴咂舌,吃掉的鱼肉喝掉的茶酒可堆成山流作河。” 另一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其开头都是不缓不急,慢慢把读者一步步带进某处独有的地域,然后才是这片地域(日本关西地区与京都)之上的人物、风物与文化一一展现——这正应了其所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川端康成极为欣赏纤细的美,喜爱用那种笔端常带悲哀,兼具象征性的语言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 最极致的例子,当属撩遍全球的普罗旺斯,这个艳阳长照之地因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及当地人爽朗的个性为无数作家所着迷进而着墨。而这应要感谢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他出身于此,坚持用普罗旺斯语进行创作,歌颂家乡的山川风物和古老文化,沉寂的普罗旺斯语就此变成活生生的文学。此后,同样出身普罗旺斯的都德以《磨坊书简》完成了地域情结的畅快宣泄。出走经年后返转的作家买下家乡的旧磨坊居住,并在此记录下亲眼目睹的一件件乡间趣事,复刻出道听途说的一桩桩奇闻传说,每一篇文字背后都隐藏着真诚的感慨,以此向前辈老诗人米斯特拉尔致敬,“沿海的普罗旺斯,山地的普罗旺斯——以及它的历史,它的习俗,它的传说,它的景色,它的纯朴的、自由的人民——在消失以前找到了自己的伟大的诗人的全体人民。” (本文系原创,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等)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shangzhouzx.com/szsqh/12697.html |
当前位置: 商州市 >作家们那些理想的远方
时间:2023/4/1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怪味小说解读语言叙事模式与美学表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